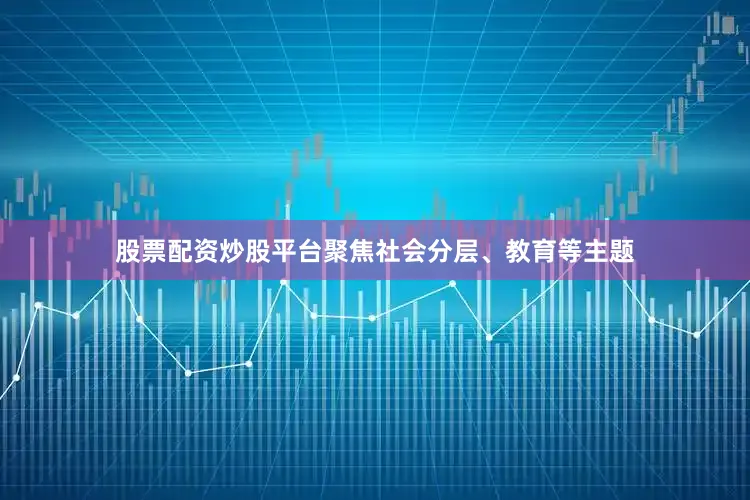来源:市场资讯
(来源:小鸟与好奇心)
如果只写牧民和马,我的意思是,如果这本书的目的是牧民和马,以及他们背后那个世界,应该也会是一本不错的书——就像《兰花窃贼》那种,或者《睡鼠说》——这是一部分非虚构著作的本职,帮你看到并理解一个你不曾知晓的世界。
但是《荒野寻马》走的是朝向自我的方向,这里面除了牧民和有马,还有森林、老工房和外婆的厨房,它们扮演的角色是相似的:作者通过它们追寻自己想要追寻的东西,在书里被表述成这样一个问题,“在庞大失序和剧烈流变之中,存在确凿不移的东西吗?”这本书不负责提供答案,它提供行动,即一个人感到巨大的困顿(尤其当这种困顿并不是生存问题的时候)之后做了什么、思考了什么。疫情之后,有人写出了自己的探索、感受,这是这本书价值所在。
经“后浪文学”授权,我们摘选了其中一章的部分内容分享给读者。
展开剩余90%骑马日记
2022 年 9 月 10 日
马马马马马
第一次坐在马背上,浑身僵硬,腿都不知道该怎么放好。对我而言,马的一切行为都是陌生的,完全不知道意味着什么。会本能地害怕。马像人类一样擤鼻子,发出呼噜噜的声响,害怕。马不肯往外走,钻回围栏,我不知道怎么控制方向让它掉头,害怕。缰绳不知道该拉到什么样的长度,手不知道该放哪,害怕。马走得太快,一头撞上前方马的屁股,害怕。马突然发出长啸嘶鸣,是要生气的意思吗?害怕。路过一片树林,马歪头去扯树叶吃,害怕。慢慢走着走着,马突然小跑了起来,本就全身紧张的我被不停抛起来,害怕。全程只有紧张,随时有掌握不了平衡就掉下去的害怕。
骑马日记
2022 年 9 月 11 日
“踢马肚子!”
“用两个脚跟踢马肚子!”
“一边踢一边发‘驾’的声音!”
这些看起来很好操作的建议,我全部难以执行。
马对它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心知肚明。
骑马日记
2022 年 9 月 12 日
回程路上,“白头心”跨过一道小沟时突然一脚踩空,整匹马往左错了一大步,我的身体也往左猛地一歪,半个身子掉了下去。眼前所有画面都变成了慢动作,我看到缰绳在以很慢的速度飞起来,听到有人在身后喊,声音模糊。
骑马日记
2022 年 9 月 14 日
听说前两天骑的小青龙受了伤,但昨天一直没在马场看到它。早上到马场时,一眼就看到了小青龙,靠近马鞍前部的背脊处,有一块两根手指长宽的破口,露出鲜红的肉,在青白的皮肤上格外扎眼。是我造成的吗?这么深的伤口之前没有被发现吗?又或者之前没伤,是我糟糕的骑术导致小青龙受伤?一边想一边在山坡上呜呜哭。
“骑马三四天就能会?学的都是什么玩意儿!”三哥垮着身子坐在马上,对右侧全神贯注小心骑马的我说,颇不屑。用几天时间和小黑哥学完骑马,我跟着三哥去赶马,小黑哥让我给他打下手。被指派这样一个跟班,难怪三哥不乐意。
三哥也是恩和牧民,平日在小黑哥的马场工作,也替人看管马群。他离了两次婚,和同一个女人,不怎么笑,也不怎么和人搭话。骑马时坐姿松散,却总骑最烈的马,马嘴勒出血还不老实。看起来很不好惹。
“就得什么马都能骑,怎么都能骑!瞅瞅才几天,就觉得自己会了?给你自己放野外能骑吗?” 三哥对我这样的城里人大概积攒了很久的不屑。唯唯诺诺点头,我努力跟上他的马。“你看,得给马信号,让它慢走就慢走,颠步就颠步,跑就跑。” 三哥演示如何精确控制马,感受缰绳力道的细微差别。但我愚钝,不得要领,马根本不听。
要赶的马群就在前方,即将穿过剪得只剩平茬的麦地,三哥放弃教学,悠绳催马,甩下我。
恩和村庄很小,在村里往任何方向走,十分钟后就会身处草原。而只要在草原里走过,自然会意识到骑马是必须习得的技能。角度很大的山坡、会整只脚陷进去的泥泞湿地、需要涉水而过的溪流,机械难以应对所有复杂环境,但马可以。它们能辨识方向,知道如何避开险境,能够轻松涉水,下山上坡。自然之中也处处都有它们的食物。比起任何一种车辆,马能让人抵达更多仅凭腿脚无法抵达的地方。
为了和马尽可能多待,我几乎每天都去马场,和牧民们学习如何照顾马。用钢梳给马刷毛,顺着马身从前往后捋,干结的灰尘在空中扬起。用手抚摸马的身体,从脖子到肩膀,健康的马毛发油亮,摸起来平顺而热。但这只是看似平和的开头。铁制马鞍沉,刚开始我一人完全无力将马鞍从平地放到马背上。做大部分事情都需要力气,这让一个只务脑力的人显得尤其笨拙。往往马师们备好了两三匹马,我还在与第一匹较劲 :总是不能顺利把那根看起来只是一根铁棍的马嚼子塞进马嘴。它紧咬牙关,不肯开口,头再一仰,我连马脸都够不到。拽着牵马绳把头往下拉,马嚼子往前一凑它又抬头。手忙脚乱,徒劳无功。活干到最后,我往往只剩把马师们备好的马牵到拴马桩去系好这一件事可做。
“不能打死结,要打专门的栓马结,有紧急情况一扯就开。”宝哥教我许多遍,但我仍过几日就忘,气恼地打上普通绳结,被三哥拍着栏杆骂。
套上全套马具,大部分马默认无法逃脱命运,顺从地候成一排。
小黑哥的马场在旅游季节做游客生意。一匹马每天的工作重复,就是载着游客走。爬山,过草原,蹚溪流,穿白桦林。慢走,颠步小跑,很少大步奔跑。游客多的时候,马几乎不休息,一趟接一趟地走。一日结束,卸掉马鞍,沾满唾液的铁棍从口中退出,摘下笼头,身上再没束缚它的东西,马扭头就跑。等所有马都卸除马具,马师们把马赶到附近草场休息。等待重复的第二日。
小鱼和我提起的马的葬礼,就发生在夏天旅游旺季的一日。
葬礼主角叫大 S,小黑哥最早拥有的马之一,为马场工作了十几年,脾性温顺,适合几乎所有类型的游客,包括老人孩子。被一个大型动物承托,一开始并不那么愉快,但大 S 是一匹不会让牧民和游客担心的马,稳重、不出差错。结果它突然死了。一个清晨,死在山坡上。重复了十几年,西西弗斯般无止境地驮运人类工作,突然被死亡中止。中止于第二日的驮运人类工作开始之前。
小黑哥查验追溯大 S 的死亡原因,最有可能的是消化不良。旺季马匹辛苦,消瘦得快,靠休息时进食的自然鲜草不够,需要牧民不时额外添加饲料,补充体能。大 S 死前一晚,小黑哥给马群添喂了谷物。没人留意到大 S 吃了多少。那天晚上吃得痛快的大 S 在想些什么?如果它会想些什么的话。这加餐真正好吃,多吃些,再多吃些。咀嚼,吞咽,咀嚼,吞咽。啊,真正好吃。
谷物从它漂亮的脖颈滑入胃里越积越多。然后它死了。
料不到大 S 这样死了,明明头天还好好的。它是伙伴,不是牲畜,小黑哥和小鱼难过,想葬了它。但哪有这样的事,马活着卖劳力,死了仍能勉强卖肉,横竖都是钱。刚死的马立刻割喉放血,卖给马肉贩子,一匹成年马出肉多,至少卖个几千元。
别的牧民骂小黑哥傻。可以卖肉不卖,非要挖坑葬,当马是人吗?那么费劲,要找拖车拖马,要找钩车挖沟。麻烦死了!马场等待骑马的游客乌泱泱,忙不迭,还有闲工夫葬马?放着送上门的钱不赚要葬马。一个畜生,死就死了。要葬你葬,我们不帮忙。
小黑哥挣扎。 “你就说卖不卖吧,我给你找人。说卖我就能给你找着人。”一位马师讲。小黑哥没出声,默许提议。马师打电话找来马肉贩子。马肉贩子站在草坡上,要剖开马肚子,看内脏还好不好。“要拿走就整匹马拿走!”小黑哥说。在山坡上剖开马肚子算怎么回事?鼓胀的肚子被划开,肠肝胃和着血,哗啦流一地。前一夜顺着漂亮脖颈吞入的也许未完全成糜的谷物也滑落一地。已经这样死了,还要被糟蹋得这样难看。
马肉贩子转头走掉。
大 S 最终的命运还是回到下葬。没几匹马的终局是入土。
拖车把大 S 带到一处坑地,是马师们每天带客人骑马时都会经过的地方。大 S 也熟悉。手边只有塑料布,便用塑料布蒙住马头,身子露在外面。人哭,拴在近处的另一匹马别过头。它来马场的年头长,和大 S 相识最久。相较之下,另一匹新来的马在旁,冷静得多。
钩车挖了深坑,大 S 葬入。人把花束放在旁侧。
马,漂亮动物。脖颈修长,皮毛光滑,肌肉线条紧实。山峦一般的脊背,从毛茸茸的耳朵往下,鬃毛顺着脖颈朝一个方向倒伏,植物种子黏杂其中。腰像水流向下弯淌,又顺着臀部顺滑地接至后腿,尾鬃垂坠。它们安静站立,与鬃毛颜色相近的睫毛卷曲,眼睛像泉。
我喜欢在所有游客离开的黄昏,趴在木栏上看马。马在围栏中,缓步,吃草。天光将暗未暗,温和的混沌。一切尚未开始,一切全部止息,一切没有目的。庞大的安静。
三位游客预约晨牧,六点抵达马场。天刚刚亮。没什么人在这个时点起得来,更少人知道这个时点骑马的妙处。备好马,小黑哥和我骑马带人上山。大地的寒意在秋天清晨无声息地冻住水汽。马走到山坡上,熹微日光照出凝结于草茎的冰晶,银光一片。不是露水,是更多被留驻的细小的剔透的晶石般的冰粒,毫无保留地折射所有穿过它们的金色光线。近处的,远处的,从任意一处回应视线,安静又热烈。马蹄踏上,发出轻微的碎裂声音。马载着我们在缓坡上跑,身体随之腾跃,向山顶,向更宽阔的落星田野。“真美啊。”所有人忍不住轻声感叹,发怔。河流结了冰,但不坚实。三哥骑马到前面去,哒哒把冰踩碎。跟在后面的马从破口过河,又回身在袒露的河面饮水。
细微声响在庞大的安静中清晰迸现,又急速消逝。
相较而言,人太吵闹了。十一国庆假期,马场客人太多忙不过来,小黑哥请我帮忙照看生意。每天的帮工都让人生气 :有人挑剔马不够高,马的毛色不够好看 ;有人显出自己很会骑马的架势,不顾牧民的安全提醒非要展示骑术,催马在不适合的地形快跑 ;有人带着几个月大的孩子出行,却只顾自己上马拍照,一路把照看幼儿的责任丢给导游,惹得导游私下里连连诉苦 ;有人说话极没礼貌,开口问询就是贬损和脏话。人的声音吵闹,欲念吵闹。
每日结束我都义愤填膺地与小黑哥痛诉,他只呵呵乐,宽慰我不要往心里去。所幸气没生几天,马场就迎来假期。呼伦贝尔的旅游季节始于五月,终于十月。每年十一国庆假期结束,餐厅民宿就纷纷关停。做季节生意的商人去往下一个目的地,村民则回到在城里买的楼房过冬。那里有集中供暖,不需要自己烧火,也不必在零下几十度的户外涉雪去上厕所。在这里,一年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是漫长假期。马也一样拥有漫长假期,出于人工饲养的成本考虑,它们会在旅游季结束后被放归野外。本地马比牛羊更有独立生存能力,能够适应零下四五十度的极寒,自己能刨开雪找草吃,找避风的林地躲藏。除非需要特别照顾的马匹才会单独带回村里马圈喂养,比如生病的马,比如落单的马。
十一国庆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,马场热闹得像过年。放马归山之前有太多工作要完成,打驱虫针,给马卸掉铁掌,以防它们在雪地打滑。马挨个被牵出来,一人抱起马腿,一人拿扳手撬开马蹄底部钉在角质层上的 U 形铁掌。但大部分马不愿配合,前蹄铁掌拔得不顺意,抬起上半身作势要用另一只蹄踢人。许多马师与抬着一条腿的马转圈拔河。
撒开!最后步骤。马们成群奔向出口,一会儿就没影了。
“马不会满山乱跑吗?找不到了怎么办?”我问小黑哥,很是担心。在马场我常展露不合时宜的慌张。有天马场门没关牢,两匹马跑了,沿着河边往下游去。我吓坏了,骑马去找正在接待游客的马师,大声通报:“两匹马跑了!一匹黑马,一匹花马,在河边!”马师不咸不淡地回应 :“没事丢不了。” 小黑哥也一样。“能跑哪去?”他反问我。
第二天,小黑哥让我和他一同去找马。马场有四十多匹马,归山后自然分群,四五匹或八九匹一群,自己找有水源有草的避风地方待。马撒出去之前,小黑哥根据往年马群分帮经验,给其中几匹领头马挂上 GPS 定位器,可以在手机上跟踪它们的轨迹。不过也有风险,万一马在地上打滚时把定位器蹭脱,或定位器没电关机,马跑到没信号的区域,人就无法通过这唯一的技术手段获知任何关于马的消息。
开车从恩和出发,我们依循 GPS 定位器的大致位置,向南经过朝阳村、向阳村,在向阳村再往南的地方找到跑得最远的小紫马。小黑哥对小紫马的表现很满意,撒出去第一天它就领着另外三匹马来到往年地点。这个组合接连几年都在一起。往回开,跑得第二远的马群有十匹,领头的叫丞相,长得稳重。这群马从小一起长大,跑不丢。接着,在路边看到小零号和小六六。小六六是在向阳村长大的马,春天才来马场,大概是想家了,带着小零号往向阳村跑。小黑哥开车把两匹马往恩和方向赶,试图赶进最近的马群。那群马里有大脖、拿铁、大 A(后来发现其实应该是小 A)、小七哥、黑花、赛巴、老丁、牵引(因为这匹马怎么都骑不出去,需要牵着,不愿意走,连小黑哥都只骑出去过两次,一次骑了半小时)。
我在粗糙得只有一条斜线表示公路走向的笔记本上,一边听小黑哥念,一边歪歪扭扭地认真记下。只是区别在于,小黑哥看着马认得出谁是谁,我只能听声写下名字。
“看,那边有小青龙。”车开到朝阳村附近,小黑哥指着远处模糊的马群说。
“噢,我看到了!”我指着那团最大的白影。
“那是大白。”大白是来马场年头最长的白马,为马敦厚。
三个多小时过去,四十多匹马都有着落,唯有秃耳朵不见踪影。
题图来自电影《马语者》
发布于:北京市盛康优配-配资门户有哪些-配资平台导航-炒股配资开户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全国前三配资排名但锻炼思维可是实打实的!)
- 下一篇:没有了